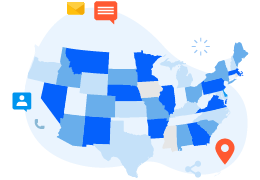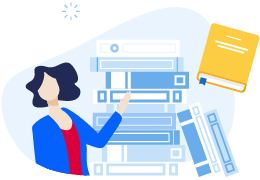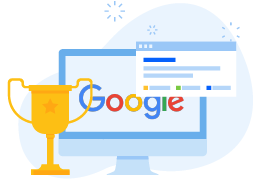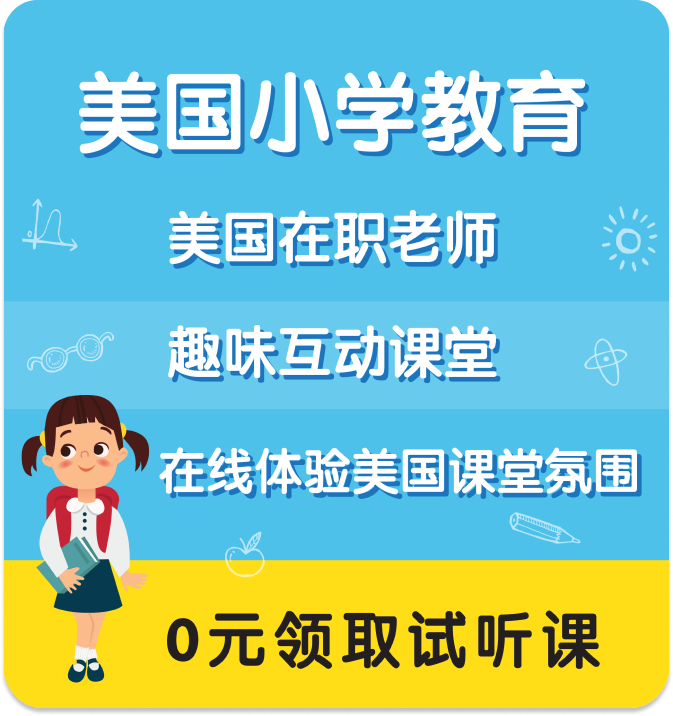欧柏林学院深度解密在美国研究中国这家小众文理学院超奇特
作者 / 唐继尧 灯塔学院特邀作者
Oberlin College 欧柏林学院哲学&政治本科在读
第一次见到 Oberlin College (欧柏林学院) 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我还在准备 SAT2 的美国历史考试。在某一本教科书上写着:first college admitted black and female students.
欧柏林学院,US News 全美文理学院排名 26 位,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创办于 1833 年,国际生比例:12%,在校人数:3000,课堂大小为 77% 的课堂大小小于 19 人,师生比例:1:11.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用潦草的笔迹将这句角落里偶然提及的话,列在了其他一些关于西部开发或者墨西哥战争的重要考点旁边——由于是自学,我对 SAT2 的难度完全缺乏概念——因而猜想在彼时还方兴未艾的西方语境的政治正确之下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考点。
大概一年后,2015 年 4 月,我接到 Oberlin 的录取通知。
欧柏林学院:全美最左倾文理学院
Oberlin College 与 Oberlin 小镇于 1833 年由长老会教士建立。学校坐落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部的市郊。位置上可以说是偏僻中的偏僻。加之学校规模又小,镇内甚至没有通向克利夫兰市区的公共交通,学校南侧 “downtown” 其实也只是一个短短的十字路口。
而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安静小镇与学校,却被称为“全美最左倾大学之一”,并且拥有悠久的政治激进运动历史。
Oberlin 建立仅仅一年后,一批来自邻近的辛辛那提州的废奴主义学生与教授,因其所属神学院投票通过反废奴条例而出走。同时,由于面临经济问题,小镇邀请由 Asa Mahan 与 John Morgan 领导的激进学生加入 Oberlin。
学生方与小镇管理者约法三章作为加入的条件:首先,Oberlin 招生时不得将种族作为考虑条件,其次,Oberlin 需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最后 Oberlin 不得干涉学院内部事务。而自此以后,Oberlin 成为了废奴运动中的先驱。1835 年 Oberlin 正式招收黑人学生。并且,Oberlin 还是当时 underground railroad(地下铁路)的一个重要站点,数千南部黑奴经此获得自由。
即使在俄亥俄州通过 fugitive slave law(反废奴法)的情况下,Oberlin College的学生仍然积极参与废奴运动。1858 年,一名逃亡黑人被邻近镇的联邦官员逮捕,Oberlin 的学生、教职工与小镇居民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游行,迫于压力镇方不得不释放被捕黑人。一系列的废奴运动使得反废奴的共和党人在俄亥俄 1860 年选举中获胜,当时俄亥俄州州长曾向当时总统 Abraham Lincoln 请求废除 fugitive slave law。
美国史上第一个招收女性学生的学院
此外,Oberlin 也是第一个招收女性学生的学院。校方于 1837 年首次招收女性学生。但是,女性学生的境遇就不是那样令人满意了,Oberlin 女性学生不但被禁止参与一些专门为男性学生开设的课程,并且校方对于女性学生的教育培养,在于使其成为能够担负家务、育儿等“女性社会任务”的家庭主妇。这情况直至较晚才有改善。
总而言之,谈到 Oberlin 的政治激进,就好像谈到中国的文明一般,对于种族性别平等,Oberlin 的“古已有之”可谓实至名归。不过,Oberlin 从来不是个甘于“我祖上曾经阔过”的精神胜利法践行者,Oberlin College 至今都被誉为“全美最为左倾大学之一”,自由主义激进运动接连不断。
这种平等精神自我初入校园时就有深刻的感受。
在入学第一天的新生欢迎会上,有新生自我介绍这个环节。
不同于我之前的经历,大家除了介绍自己的姓名、籍贯、爱好一类的信息外,高年级学长学姐还要求我们注明“自我性别认同称谓”,也就是英语中的第三人称称谓。这是 LGBTQ 运动发展的一个潮流:PGP 自我性别认同称谓(preferred gender pronoun)不仅欢迎 transgender 使用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 she/her/her与he/him/his,同时还有 queer 群体偏好的 they/them/their。
LGBTQ 平权运动下,呼应着 PGP,学生对宿舍内的卫生间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每个宿舍通过投票的方式基本取消了男与女的卫生间划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尊重多元化的 E 系统:在每个卫生间门口都有一个可以扭动的 “E”,E 代表 everyone(所有性别一起使用);躺倒的 E 则是 “W”,women only(只有女性可以使用);趴下的 E(趴下和躺倒纯粹是直觉区分)是“M”,men only(只有男性可以使用)。平时默认的设定是 E,everyone,而如果有人觉得不适时,可以在自己进入时把 E 调整成自己偏好的选择。
关于浴室洗手间取消两性区别的讨论去年也进入了中国的视野,在许多人眼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灾难:对偷窥、性侵等犯罪行为的恐惧,甚至对要实行此改革的原因—— LGBTQ 平权——本身的不赞成或者漠视,使得这个话题几乎成为“中国真好”的一个证据。
但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革在一校的实施不代表在所有学校甚至社会的实施——这一方面是精英主义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是渐进改革的应有表现。以 Oberlin 为例,这样的改革本身是依靠直接民主的方式决定,而非由如最高法院判决 LGBTQ 般由一党或一人推行,其可行性具有直接民主所能提供的保障。
积极参与政治运动
在美国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Oberlin 毕业的学生也是颇为积极。
即使像我一般,在大学的头两年中集中精力关注哲学政治理论,对陌生国家的实际政治运动保持悬置观望态度的学生,也能透过身边同学老师的言行甚至课堂内容的方方面面,认识到当前美国最激进的政治潮流在 Oberlin 的影响。
我的指导教授,政治系教授 Marc Blecher 常常对我们谈起 Oberlin 学生对于实际政治的积极参与。他说,根据统计,2011 年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第一天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里,就有 10% 毕业于总学生数区区两千多人的 Oberlin College。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曾是我的学生。”Marc 总要补充这样一句。微笑之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
Marc Blecher 戴细框圆眼镜,犹太人健康红润的肤色,蓄半寸短胡须,还未受秃顶折磨的银发剪成干净利落的平头。他个子不高,却身材壮硕,下午工作时书桌边的 mozzarella 奶酪切片与乐事薯片使他的腹部近年来像海豹一般脂肪丰富。
Marc 毕业于 1969 年的康奈尔大学,随后分别在 72 年与 78 年,师承中国政治学者邹谠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在已是 Oberlin 资历最老的教授之一的他,六十年代末是万千与美国政府斗争的反越战运动激进学生中的一员。
在美国,研究中国
而谈起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以及学术道路的开始,Marc 总要讲起反越战运动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以及那时毛泽东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
“……我们要反对 Lyndon Johnson(美国第 36 任总统),我们要攻击我们的政府。而那时的中国在干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政府的首脑,他自己竟然说革命有理,鼓励学生攻击政府!我一下子就被这个国家,被社会主义吸引住了…当然,当然,后来等我开始学习中国政治,我就知道,世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对 Marc 的印象,仅仅是浏览 Marc 的简历时看到,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反潮流的中国》,曾在 1998 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
说来惭愧,就凭借这两点,我便先对 Marc 形成了简单的刻板印象——我毫不犹豫地先将 Marc 归类为王小波笔下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幻想红卫兵的“美国左派”了。当然,庆幸的是,如同 Marc 学习中国政治时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不简单”一样,只用几节课,我便知道 Marc 的“不简单”。
我跟随 Marc 选修的第一节政治课是他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一门基础国际政治课。在这一节课中,Marc 引入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与国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两个要素作为理论基础,以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关系作为本门课的研究对象。
国家能力这一政治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时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国家能力强的政府往往能够有效地颁布并实施政令,而国家能力弱的政府则往往出现出台新政艰难,以及政策成为一纸空文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与“社会”相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程度。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息息相关互相影响,故而,也有的理论家认为二者其实是同一概念或从属关系。
Marc 正是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角度切入,以文革前中后中国期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变展示出“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涨落,并分析这一理论所能解释的复杂政治经济学后果。而其中令我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一理论应用在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之中的解释力。
Marc 指出,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使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在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中皆遭受瓦解或削弱,也就是说,不仅广大民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惨剧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精英的党政机要更是对群众的自发革命路线心有余悸。而在这一情形下,新经济改革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经济发展来重建政府合法性与维持社会的稳定。
然而,市场经济改革不仅仅要触动无数工人与工业计划经济官员的既得利益,而且更要实行价格改革,必然导致普遍的通货膨胀,也就说相比于壮士断腕,改革更像是一将功成。
“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正准备去河南农村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研究,”Marc 讲道,“有一天早上我突然看到大街上的商店门口排满了长队,我很惊讶地问排队的人,这是有什么打折活动吗?他们答说,没有,只是因为报纸上说最近会价格改革,以后钱就不值钱了,我们看到不管什么就先买下来……就是这样的担忧焦虑下,几天之后那次价格改革便宣布取消。”
于是八十年代政治经济最为矛盾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必须通过新的经济改革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推行一定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就在这个矛盾下,中国的八十年代见证了缓慢而艰难的市场经济改革。比如臭名昭著的双轨制,不仅淤塞改革,还滋生了广泛的权钱交易。
而这个矛盾的突破口正在于国家权力与国家自主性在八十年代末的重建。Marc 分析道,八十年代末,中国“因祸得福”,用重获了强大程度与文革前媲美的国家能力与自主性。到九十年代时,政府绝不需要再担心,下岗等问题产生危机社会稳定的不满。这一国家能力飞跃最终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推力。之前人心惶惶而不得不几次三番推迟的价格改革与大规模的工人下岗,都在九十年代飞速展开。
Marc 对这一深化新经济的分析,采取了“国家能力”的角度,首先,这使得比起国内许多回忆起那个年代,将九十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市场经济,都归咎于“对家国大事的失望堕落”而导致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扎实基础,显然更有说服力。其次,这个分析与 Marc 一以贯之的对新自由主义批判也相一致。“这个历史告诉了我们,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行,远远不是一个“恢复人类天性”的幸福圆满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它是压迫(coercion)与劝教(persuasion)的结果。这是当代政治中对于 Gramsci 所提出的 hegemony 概念的教科书范例。”
正是敏锐发现了这一条脉络,九十年代,Marc 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一次,他的学术课题正是天津市下岗工人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Hegemony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中,Marc 在他采访与观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激进并享有无数特权的工人群体,面对经济改革带来的困境时表现出的吊诡沉默。而 Marc 给出的答案,正是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合法性这一组 hegemony 的建立。
Marc 的论点对于在国内两种极端话语语境下曾从一方反叛到另一方的我,有着独特的颠覆性启发。在高中时期,对教科书、对教条的反叛与否定,使我盲目地接受了我所根本不了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Marc 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接下来我所选修的更为宏观地研究整个东亚采取的高国家能力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东亚政治经济学”。这对于在中国某些语境下几乎成为“真理”代名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力的批评。
探索学术这座冰山
作为一个“美国左派”,反越战对于 Marc 来说,显然远远超越了一次“反政府的叛逆狂欢”。这一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政府和平运动,不仅仅引起了 Marc 对政治学的兴趣,更成为帮助 Marc 以后政治学研究的宝贵经验知识,使他理解前人理论家所面临的人类共同的难题与境遇。而他通过课堂,将这一经验知识又分享给他的学生。
当我这一学期进入爆满的马克思政治理论课,开始阅读马克思、Gramsci、法兰克福学派……我感到政治学像一座深埋水下的庞大冰山,我最多只能算刚刚触摸到水面。
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对于 Marc 的影响,就好像 Marc 对我的影响:他给我展示了这冰山的一角,这使得我可以去发现这整座冰山,并且同时不断提醒自己,在了解它真正的深度与广度之前,不要妄下判断。
即刻开始申请咨询
扫码比肯,备注“申请咨询”
比肯私人微信号:lighthousewatcher
你还可以直接给灯塔拨电话
灯塔咨询热线 010 6518 7867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Dreamgo网站,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copyright@dreamgo.com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info@dreamgo.com